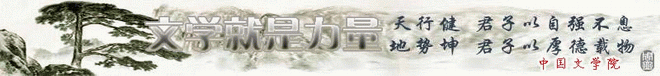- 第七章 一 流金溢彩的金铜造像
- 作者: 李 吏 日期:2012/7/16 17:03:14 阅读:456 次 [大 中 小]
-
第七章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以及法器
一、流金溢彩的金铜造像
在藏传佛教寺院的殿堂内,金铜造像在香烟氤氲灯明闪烁的气氛中显得异常的神秘庄严。这些雕塑艺术品,大都玲珑剔透、美观大方,令人赏心悦目,百看不厌。金铜佛像,藏语称为“利玛”,指各类响铜制品,又特指东印度铜佛像。在绚丽多彩的藏传佛教艺术中,藏传金铜佛像作为雕塑艺术的一个主要门类成就骄人,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之林中绽放着奇异光彩。这些佛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,反映出雪域高原人民对美非凡的感悟力和卓越的创造才能。
藏传佛教众多大寺院都有利玛拉康,收藏寺内的贵重佛像。藏族金铜佛像雕塑工艺有两种:铸造与打制。其中大部分是金属浇铸的圆雕佛像,使用材料多为各种铜合金,一般分为红铜、黄铜、青铜,实际上所用铜的种类很多。早在16世纪,西藏噶举派僧人白玛噶波就著书描述关于各种利玛以及印度、尼泊尔、西藏、汉地、蒙古各地佛像的特点,就材质与风格对藏传铜佛作了分类,有花利玛、白利玛、黄利玛、红利玛、紫利玛、桑塘玛等各种利玛佛像。其产地可分印度、蒙古、尼泊尔、汉地、西藏利玛佛像。
藏传佛教金铜佛像数目浩繁,种类繁多。就其内容而言,主要可以分为显宗、密宗、传承祖师三大类。
显宗类佛像,在各大佛教寺院占有 相当大的比例。佛像造型变化多端,纷繁复杂,令人眼光缭乱。其特点一般是慈眉善目、面相庄严。代表作品如释迦牟尼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弥勒佛、金刚手菩萨、无量寿佛。造像人物稳坐莲台,神态安祥,周围或用莲花或用光环相衬。
密宗佛像,在众多的神像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。青面獠牙、多头多臂、牛头马面、瞠目攒拳的造像在寺院殿堂里比比皆是。佛教认为这些极为狰狞可怖的佛像是佛和菩萨的忿怒幻化身,如时轮金刚、胜乐金刚、集密金刚、马头金刚、空行佛母神像。表示以武力消除佛教徒们修习正法时的种种邪见违缘,降伏一切危害佛教的邪魔外道。他们在好人眼中都是慈悲美好的,而只有在恶人眼中才是极为恐怖可怕的。
传承祖师类佛像,主要分布在格鲁派各寺院中。典型造像如宗喀巴师徒三尊、历辈达赖喇嘛、班禅大师以及藏传佛教其它各教派传承的高僧大德。这类造像内容多为历史上雪域文化本土的高僧。
藏传佛教历史悠久,流传地域广泛,藏传金铜佛像艺术形式的变化折射出多种艺术来源的相互影响,因此多种地域风格是它的突出特点。藏族艺术家们善于吸收汉地、印度、尼泊尔、中亚各地的艺术营养,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雕塑艺术的基础上,兼容并蓄,博采众长,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醇厚地方特色的艺术类型。在金铜造像制作过程中,不同的流派,表现出不同的风格,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。按地域风格,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艺术风格可划分为外国风格、本土风格以及内地风格。三种风格在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:
1、外国风格。该风格的造像有斯瓦特、喀什米尔、东北印度、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特点。
斯瓦特即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,属古犍陀罗,当时这里的佛教曾十分兴盛。出生在这个地区的莲花生大师于公元八世纪中叶来到西藏地区,弘传密宗教法,成为西藏的密宗祖师。藏族人一直将该地区看成是佛教的圣地。犍陀罗艺术也就随之在西藏传播开来。犍陀罗佛教艺术,可以说是印度佛教的内容与希腊、罗马的雕刻艺术结合而产生的。作品的特点表现为佛陀多着通肩式披衣,衣服褶纹起伏很大,立体感强,衣纹走向从右上往下倾斜,左手习惯性地抓握着大衣的一角,头发呈水波状或涡卷状,覆盖着肉髻,鼻梁与额头成一线,凹目高鼻,薄唇,蓄有两撇上翘的小胡须;菩萨穿裙,袒上身,上身往往搭裹一条布,从左肩搭于右手上,颈部饰有颈圈、项链、璎络等物,形体健壮,身材粗短,姿态有力,犹如年轻的男性武士,头发很浓,发型翻卷,为束扎头发,头发正中有方型饰物和大花卷,宝增在脑后结为四根,在两耳侧如蝴蝶般飞舞飘扬,耳朵上有耳饰。佛、菩萨像大多有同心圆形光背,下为四方形台座,台座四周刻供养人,左右为两个狮子,中间置水瓶花叶。
喀什米尔在印度西北喜马拉雅山区,公元十世纪末佛教在西藏复兴,喀什米尔佛教艺术也传入西藏,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作品特点表现为人物的造型脸形长圆,眼睑大开,瞳仁点在正中,似吃惊状,有的眼大无神,身躯饱满。佛像多着袒左肩袈裟,上身比例略长,通身用黄铜铸造,光滑亮丽,台座形式多样。代表作品如燃灯古佛,方屋型台座,左右两侧跪供养人,佛作说法印,神态安祥亲切,袒右肩,裂装衣褶用凹沟表现,自然流畅,黄铜铸造,光亮滑润,是难得的艺术珍品。
东北印度,公元740年帕拉王朝在孟力拉地方兴起,该王朝推崇佛教,八世纪后成为迅速衰落的印度佛教的最后据点。十世纪初该国高僧阿底峡在西藏传法长达17年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西藏的利玛佛像造型带有浓厚的帕拉造像风格。帕拉造像建立在笼多美术基础上,东北印度本土特色浓厚,与喀什米尔造像在某些细节上相互影响,但风格迥然有别。帕拉造像的面貌颇具印度人特点,如眼脸突显,嘴唇丰厚,眼大有神,形体粗壮,身材曲线流畅圆润,薄衣贴体近乎全裸,只在肩头腿部有简单的衣纹刻画。代表作品如桑唐利玛毗卢佛,黄铜铸造,镶嵌宝石、银丝、红铜丝,华丽精美;半月型台座,前雕三位供养人,左右两匹马,边缘刻有齿形火焰纹;顶部雕小伞盖,头光雕为菊花形;莲花座下加多层折角方台,造型生动,工艺绝妙。
尼泊尔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尼泊尔与西藏地域相连,自古以来经济文化艺术关系紧密。吐蕃时期,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,携佛像经典和尼泊尔工匠到西藏,修建大昭寺传播佛教。尼泊尔工匠长期在西藏工作,西藏佛教艺术与尼泊尔艺术有着密切联系,特别是13世纪后印度佛教灭寂,印度佛教艺术对西藏影响甚微,使尼泊尔艺术影响更为深广,不仅在西藏,而且扩大到中原内地。元代尼泊尔匠师阿尼哥随八思巴国师来到大都,长期主持宫廷绘塑之作,以其卓越技艺受到朝廷重用,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,把尼泊尔、西藏的金工技艺及佛像传播内地,留下一段中尼友好的千古佳话。
2、本土风格。由于藏族地区地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,造像艺术也深受这些毗邻地区风格的影响,表现为佛像普遍造型粗犷、朴实,比例、动态上不太协调,有一种儿童画式的稚拙感,纯朴可爱,童趣盎然,反映出藏传佛教雕塑童年期的面貌。藏族工匠在仿造外来形式的过程中,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,逐渐形成本民族的风格。尤其是十三世纪以后,西藏纳入祖国版图,相对统一的政治局面必然对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不同艺术流派相互影响,逐渐融为一体,形成一种更为统一的表达方式。这种统一的风格,表现为佛像造型的帽冠装饰、莲座背光形式基本一致,印度、尼泊尔等外来影响已不明显。佛像造型摈弃了早期的传统,出现了不少创新的作品。代表作品如四臂观音,宽额尖下领,藏族特征明显,手法简洁洗练,庄严而生动。
3、内地风格。自七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后,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。十三世纪后,藏区与内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联系更加密切,元、明、清中央政府都大力扶植藏传佛教。15世纪后西藏佛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吸收了汉地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,汉藏艺术双向交流,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发展的主流。内地的造像中以元、明、清三朝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最具代表性,如明代制作的大黑天,铁镀金像,肌肉裸露部位是铁的黑色,宝冠璎络飘带等处镀金,弯刀为银制,色彩对比鲜明,全身披挂网状繁密的璎络珠饰,雕刻精细,一丝不苟,是永乐造像中的珍品。这种造像,虽遵从藏传佛教造像的规则,但却融汇了汉族雕像的表现方法,如方正的脸形,写实的服饰,注重细节刻画,精雕细琢,虽不及西藏本土造像形象生动,但其精美华丽却胜过西藏本土作品。清朝历代皇帝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,干隆时期,在皇宫内外广建寺院,大造佛像,代表作品如大威德金刚,是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中最繁杂的一尊,此像工艺精湛,繁而不乱,身姿右高左低,形成强劲动势,而又不失平衡。另外在西藏极负盛名的有拉萨大昭寺供奉的“觉卧佛像”,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拉萨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,为詹金铜佛。
布达拉宫金碧辉煌的红宫内有一座小殿堂——利玛拉康,即响铜佛殿,这是一处进深不宽的狭长殿堂,面积不大,没有高大的佛像、灵塔,亦没有华丽的装饰,不大为人注意,实际上这里专门收藏各类利玛佛像,集中了西藏金铜佛像的精华。当年五世达赖喇嘛对这个响铜佛殿是十分重视的。布达拉宫响铜佛殿珍藏的金铜佛像有三千多尊,数量众多,精品荟萃,佛像基本为一米以下的中小型,小佛像易于保藏,得以长久流传。藏族对古响铜铸造的佛像,视为比纯金造佛像更为贵重其内有大量古代佛像珍品,具有题材丰富,历史悠久,地域广泛,艺术风格多样的鲜明特点,既有汉地所造佛像,也有印度、尼泊尔古佛像,最多的当然还是西藏各个时期的佛像精品,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,精美绝伦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。传世的藏传铜像数量极大,不仅在西藏,内地也有大量收藏,国外也有不少公私收藏,论数量品质难有出其右者,恐怕只有北京故宫的皇家收藏堪与其比美。
例如,其中的一尊绿衣救度佛母像,高32.5厘米,是西藏14世纪作品。绿度母戴独叶珠宝冠,神态庄严和悦,耳佩大耳铛,束发冠戴在耳两侧翻卷,袒露上身,佩带项链、臂钏。丰乳细腰,肌肤圆润,左手握莲花茎,右手施与愿印,两肩旁雕盛开的莲花,花茎弯曲粗壮,左腿盘曲,右腿伸出踏小莲花,身躯略侧扭,体态优美典雅。白度母、绿度母,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,是藏传佛教中形象最秀丽的女神,深受敬奉,是藏传佛教中的重要题材,所以传世的白度母、绿度母铜像数量众多。西藏民间传说松赞干布的两位王妃尼泊尔墀尊公主、大唐文成公主,是两位度母的化身,得到藏族人民永久的爱戴与怀念。在布达拉宫、大昭寺以及众多的寺院殿堂中都可看到她们的塑像。藏传佛教诸神中女神众多,藏族艺术家们把对人体的审美标准运用在佛母的塑像上,大胆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。
另外的一尊积光佛母,高29厘米,三头八臂。全跏跌坐于莲台上,有一头大猪驮载,造型奇特。积光佛母也称摩利支天,本是印度教中猪首人身的光明女神,摩利支即“威光”、“阳焰”之意,也译称“作明佛母”她后为藏密所吸纳,变为三面八臂的独特造型。此像三面中的一面多为猪脸,表明女神的原始身份,佛母面容端庄丰满,具有汉地佛像特征。八臂各持金刚杵、弓、无忧树枝、金刚索、线等法器。佛母上身赤裸,胸前装饰华丽的项链璎珞,写实的衣褶起伏自然,精雕细刻镀金亮丽,是汉藏佛像艺术的完美结合。此像1992年曾在故宫博物院展出,莲座后刻有“大明永乐年施”题记,是明代永乐时期宫廷作品。
在拉卜楞寺也收藏了数量巨大的金铜造像。其中在寿安殿供奉的一尊狮子吼佛像是铜塑鎏金像,高900公分,宽443公分,并有巨型靠背。狮子吼佛,藏语称“桑盖俄绕”,据说宗喀巴大师是该佛的化身,其在未来世界从其手持的宝梯上降世,在人间普度众生,讲经说法。据说该塑像体内装藏着如来舍利,宗喀巴大师的发舍利,三世达赖供奉过的宗喀巴佛像,以及印度、西藏大成就者的发舍利、法衣多件。
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,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,在继承本民族传统造型艺术的基础上,与周边地区民族文化交流所取得的辉煌成就。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,值得我们去仔细观赏和品位。
- 第一节、第七章 一 流金溢彩的金铜造像 [ 返回主目录 ] 下一节、二 神秘威严的宗教法器
杂志约稿 |
||||||||||||
|
||||||||||||
 网址:http://www.chinanwa.com
电子邮箱:
网址:http://www.chinanwa.com
电子邮箱: 1009068986@qq.com
1009068986@qq.com
 微信:18001145010 QQ
微信:18001145010 QQ 1009068986
1009068986  创作群195592079(已满)
创作群195592079(已满)  中国网络作家联盟群136849320 ;
中国网络作家联盟群136849320 ;
- 版权所有:
 『 网络作家网』 网络支持: 中网协
『 网络作家网』 网络支持: 中网协
-
Copyright ◎ 2003-2020 www.chinanwa.com All Rights Reserved
 京ICP备18029743号-5
京ICP备18029743号-5